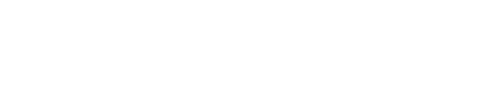蓉城四月,天气暖好,街上草青叶润,春花娇媚,端是一派安宁静好的景象。在青砖红瓦的小巷深处,淡紫色的泡桐如霞如雾,此时正是午后三点,她刚从咖啡馆换完班,角落里拖着肚皮的猫垂下倒刺的舌头,一下又一下舔舐她扔去的残食。连着好几天的晚班,让她困倦地不行。她随意拍拍猫的背脊,在路边随手折了一支泡桐,塞进包里,往住处走去。
一进门,她窗帘也不拉,单手脱掉上衣,抱着枕头倒进沙发里,她想迅速有一场酣睡。桌上的木纹花瓶里垂萎着几朵败了颜色的花,她半阖着眼,揉搓着那支饱满的泡桐,任由绿色的汁液沾染上拇指,再啪嗒一声,落入颈间。温热又粘腻的触感如蜜蜂的尾针,猛地扎入她敏感的神经,她突然发起怒来。
已经在蓉城住了半个月了,钱包越来越空,母亲的电话越来越频。天真的母亲认为她还在朋友家住着,可是哪里还有什么朋友呢?刚生病那段时间还好,随着她脾气越来越古怪孤僻,朋友们每每想关心她,都被她那冷淡的、怀疑的眼神刺回来,久而久之,她真正变成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了。还记得一年以前的日子,她在A城的那所大学和好友们谈天说地,纵情欢笑,纵然是极不喜欢的专业但务实地想着工作前景,也就读下去了。她那时每月回一次家,等母亲下班回来一起吃饭,桌上虽无甚佳肴,母女两人也吃得温馨快乐。到底有多久未曾和母亲一起好好吃饭了?她蛮横地揉了揉眼睛,将那朵泡桐一把扔到了桌上,和前日未曾收拾的残羹混在一起,紧闭上眼,终于睡着了。
送货的地方叫“青梅小院”,是城南一所民宿。正如其名,那院子里有一颗枝繁叶茂的青梅树,年年挂果,如今已成为民宿老板向外宣传的一景。此时正值四月,正是那绿梅树落花结果的时候,她送完了货便坐在那园中石凳上小憩,抬眼望去只觉那梅树绿深一片,依稀可见几个圆小的梅果。后院本就静极了,她竟未能发觉身后站着一个拎着编织袋的老头。那老头,老的惊人,也瘦的惊人,若不是拎着袋子,实在让人怀疑那空荡荡的衣袖里是否还有手臂。他颤巍巍地走到树前,伸出满是褐斑的手,缓缓压上了梅树紫褐色的树干。也许是这情形太过奇怪,又或者是这老人实在老的惊人,她不禁被这副画面牵引也来到了梅树旁,正当她站定,那老者却突然转过头来,只见一张掉了漆的木偶脸,瞪着浑浊的眼珠古怪的瞟了她一眼,随后摆着破败的身子,摇摇晃晃的离开了小院。
回程的路上,她沿着墙角慢慢的走着,四月的光穿过树叶一个个孔隙,斜斜地打在光滑的路面,她一个个的踩过去,仿佛在戳破每一个气泡。
是时候换个地方了,现在她的决定‘永远’做的迅速而潦草。
她的新住处在朝南一面的三楼,比原来那处稍大一些,整个房间是以淡绿色为主调的装潢,沙发正上方悬着三幅小小的油画,色彩明艳用笔洒然,让素淡的房间多了几分活力。
住进的第一天,夜里淅沥淅沥下了一晚的雨。清早起来,窗外的一切都显得明润透亮,不知名的鸟雀蹲在遮雨棚上清脆地啼着,她伸展着身体,感受肌肤与棉被轻柔地摩擦,空气中氤氲着清新的凉意,她的小腿肚情不自禁颤了一下。她直起身来,赤着角走到窗边,掀起窗帘,望向那株老梅。后院果然很是清幽,老梅静静伫立在那,仿佛自成一片天地。她走下楼,只觉梅叶片片翠亮,凝出几滴水珠来,打在她的额头。她学着上次那个老人,把手按在梅树糙劲的紫褐色枝干上。坚硬的树皮遍布曲折的纹理扎在她掌心几处,伴随着浓郁的凉意,她慢慢摩梭了一番,揣度着这树的年纪。
“树啊!树啊!。”她听到几声沙哑深沉的低喊,仿佛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,从胸腔里费力地挤出来。竟又是上次那个老头,她防备地看着他,心里冷冷地想着。
那老头也不理会她的冷眼,只是拍着梅树的树干,摇着他破败的身子,坐到石凳上,指着那株梅树,自顾自地说起话来。
“以前咱家的院子就只剩一个你咯。哈?”那老头摆摆手,“我越老越没用,你却是愈老愈壮了。” “你摇几个果子给我?“那老头嘿嘿的笑了几声,瞪着他浑浊的眼珠,拍着手走出了小院。
风从南面吹来,又摇动几颗水珠,落入她的后颈,她往后抹了一把,抬起头凝视着那树,仿佛看见福贵牵着他的牛在树干里走着……
每到黄昏清晨,她便来到后院,在这片幽静的空间里独处。除此之外的时间,她都在前院工作。原来是民宿的老板听闻她要在此地长住,民宿内又刚好缺人手,便许了她2000元的工资,让她做一个月的帮工。民宿老板酷爱咖啡,有一套完整的咖啡用具,她偶尔会帮着做上一杯。此时正是午后一点,民宿没什么客人,她手冲了一杯咖啡,正耐着心等着棕色的液体缓缓从银色的壶中流出,咖啡沉沉的气味一点点渗入潮湿的木头,她耸着鼻子深吸这混合着霉味的特殊香气。
不远处有一本被折了角的国家地理杂志躺在置物架上,一只骨节分明的手顺着折角将书翻开,天幕所垂之处是一片广袤无垠的戈壁,云沙相接处,尽是天风浪浪,落日熔金,那只大手抚平被卷起的流沙一角,“古尔班通古特沙漠,在新疆准噶尔盆地,这地儿你听说过吗?”她摇摇头,继而又点点头。那手的主人抽出椅子顺势一坐,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木制骆驼,准确地抛过来,“从那带来的,他们都有。”
这是一个善谈的男人,三言两语间她已经知道了他名叫韩烁,也是民宿的帮工,边打工便旅行已有一年,去年这个时候也是在蓉城落脚,是这家民宿的老客人。
“你经常跑到后院去。”那人凑到壶前,深吸了一口,她皱着眉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,她不惯与人离得这么近。
“对不住,在牧区呆久了。”他抬起头,一双黑亮的眸子定定的看着她。
“你一定碰到过老梅了吧,他经常来这边晃。”
“老梅?”她有些不解,但她沉默惯了,并未开口询问。
他拍了拍头,突然咧嘴笑了起来,“忘了你刚来不久,这老梅不是后院那颗老梅,是住在附近的一个老人家,姓梅,这里以前是他家的院子。”
她低头清洗用具,闻言微微点头。那人继续说下去,“老梅年纪大了,神智有些不清,有时候喜怒无常,你碰到他躲着走便好。“
她将杯碟依序摆好,那人已倚坐在沙发上翻着杂志,她递了一杯给他,便寻了另一边坐下,“你同那老人家很熟悉?”
他合上杂志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,“也不能说熟悉,只是有空总会去看他几眼。”
“说到这,也有好一阵没去看他了。你是在后院碰到过他?”
她点点头,“四五天前见过。”
那人闻此沉默了几瞬,随即开口问道,“不如今日一起去看看他?”语气轻柔而又郑重,或许是今日咖啡的香气太好,她不自觉点了点头。
顺着民宿所在的街往前走两个街口,拐进一个狭长冷清的小巷,有一扇锈迹斑斑且是半开着的门,两人默不作声地走进去,他敲了敲铁门,冲里头喊了一声,“老梅”,无人应答,她跟在身后,侧目看着门里的光景,屋内黑漆漆的一片,只有最深处的黄框玻璃窗还透着一些光亮。他领着她穿过狭小的客厅,拐了个小弯,直径走到最里面的屋室,他又叫了一声“老梅”。一个穿白背心的老人,慢慢从床上坐起,张着嘴瞧着两人。他指着韩烁,叫他坐下,随后偏着头望着她,似乎在思索。韩烁连忙拉着她也坐下,对那老梅说,也是院子里的人。那老人点点头,摇摇摆摆地走到床后,摸出几个皱皱的橘子,叫他们吃。
韩烁拿着橘子,蹲到老人身边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木雕骆驼,放到老人手上。那老人惊喜地望着韩烁,用手将那木骆驼托起,凑在眼边细细的看。两人又低声交谈了几句,随后韩烁扶着老人睡下,两人轻轻走出了小屋。
“今天老梅难得很清醒。”快要走出小巷时,他回头看了看那屋子。她也低头嗯一声。
“你为什么要叫他‘老梅’?” “是去年我刚认识老梅,他叫我这么称呼他的,老梅说他现在已经无亲无友,我这么称呼他,他会觉得依稀还有老友亲人在身边。”
她点点头,两相无话。后来他们又结伴去看了老梅几次,都是一些和今日差不多的光景,自不必再叙述。
每个晚上,当民宿的工作完毕,她都会躺在床上,望着白色的天花板,任凭思绪发散。屋内光影如潮汐般渐渐退场,待她醒来,窗外已是月白星微。她的思维还有些混沌,只觉做了一场好长的梦,她独自一人踱着步不自觉走到后院,只见院中月光并不均匀,只将几束光影沿着墙照在低矮的灌木从中,而梅树的枝干却是完全融进黑夜里,只看得见几团叶的阴影。
“丁甜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叫她。“真是你,你今天也睡不着觉吗?”
她本还有些怵这黑夜的幽森,如今见到一个熟人,虽然她离群索居惯了,此刻也有几分真切的欢喜。
两人坐到院中的石凳上,“你很喜欢这颗梅树?”韩烁用手电筒照向那颗老梅。
她摇摇头,“我只是喜欢这的安静。”
“你来蓉城多久了?”
“快一个月了。”她抬着头望着那轮银月。
“你想家了?”他不确切地问出口。
“你呢,你已经在外面旅游了一年了吧。你想家吗?”她扭过头来反问他。
“我没有家。”他也抬着头看向月亮。
她不知道说什么,只能点点头。
“你为什么要出来一个人旅行?”
今夜真是静极了,只有灌木从中几只未眠的虫儿还在微弱地叫一两声,她突然很想把心事都说出来。
“我害怕时间,或者说我害怕未来。”她顿了顿,继续说,“我根本不敢想未来是什么样子,我总觉得只要我想了,就能把我的人生一眼望到底。” ,“有时候我看着这颗树,就常在想要是我是一颗树就好了,只需要想着如何生长壮大,光阴于一棵树而言只是那几圈年轮而已。”
他摆摆手,站起身来,示意丁甜往外走。
“其实我应该懂你说的意思,一年前我来到蓉城,碰到了老梅。”
“当时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来处也没有归处的人,我不知道自己生活是为了什么,便辞了职想通过旅行寻找答案。”
他们走到堂前,“老梅当时脑子还很清醒,他和我说他活了快80年,他这一生,命运让他承受什么,他就接受什么,固守在这一处的人生里。等到老了,回望这一生,才慢慢意识到他从没有主动选择过开辟新的生活,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。”
“他和我说,人生其实还有很多种可能,但是人往往只看得到眼前的一条路。你不走出去,不碰撞,就根本看不到新的天地。”
她沉默地听着,想着那个老瘦的身影。
“新疆真的很美,我决定去那边支教几年,或许我将来会一直生活在那里。”他停下步子,用那双黑亮的眸子认真地看着她说,“我相信你一定也能找到一条新的路,到时候你会发现纵然未来再不清楚,至少你现在在做你想做的事。”
“夜深了,早点回去睡吧,明日我就要走了,希望你能来送送我。”
她站在门口,望着这年轻的脸庞,轻轻的点了点头。
回到房间,她抱着枕头坐到窗台上,那枚木制骆驼立在角落,朝着窗外,静默的站着。她随手抓了过来,让它矗在自己掌心。夜果然深了,她阖上双眼,漂浮着的意识在混沌的一角搭建起了一座黄沙古城,那里有暗红的绸,悬缠着挂角的哑铃当,在风沙中一下又一下的闷晃,系着绯红纱巾的老板娘慵懒地搅晃坛中琥珀色的浆液,闪电劈开乌云,耀出一道惨白的光,她知道远方有骑马的客人在雷声中赶来…… 于是,她骑上木骆驼,跃进老梅树的树干,莹绿的叶子在翻涌着的流沙中闪着透润的光,原来,这是一条新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