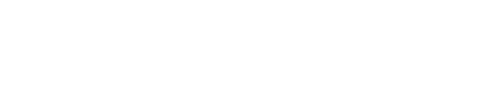弥漫的水,湿冷的水,粘稠的水缓慢地从潮湿阴暗之处爬来,浸透着一切,带给人湿冷窒息的感知。吸饱了水雾的恶之花,摇曳着从被埋藏的意识中盛开,张扬地散发出怀疑,愤恨,秽恶的气味,这是雾中的一切。
降雾以来,太阳被水汽遮盖,浓雾封锁了视觉,闭锁的环境让身体与意识的感知变得格外清晰。温度与光的缺失搭建起一个让人无法正常生存的世界。降雾的第一天,混乱还未曾来临,“和睦的一家”在浓雾的夜晚一齐涌向储藏室,电炉制造了一个热气腾腾的空间,“大家挤在一起流汗,一直流到早上”,这是无法挣脱的水,“汗液”让一切再度变得湿淋淋,逃难失败;降雾的第二天,雾气更浓,“太阳变成了淡蓝色,被裹在很长的绒毛里”,骚乱在无法改变的处境里爆发,家人失去了“原形”,变得急躁,古怪,甚至轻佻。母亲离家出走,父亲的身子若隐若现的浮在雾中,轻佻古怪的话语从脖颈处传来,两个哥哥拖着残败的身躯嚣张发狂……人们靠着冲动与狂躁在迷雾中与恐惧对峙,在可怖的世界里,心底最深的记忆,隐藏压抑的冲动,蠢蠢欲动,恶之花吸饱了水分开始含苞待放。
作者的笔尽情涂抹,在人物结束了最初的情绪发泄后,雾中的生活开始陷入了最深的混乱。人的记忆与理智变得错乱,恶意与猜度构成了雾中最真实的人际关系。母亲对于二十年前的蛋耿耿于怀,记忆迷失在过去的空间;父亲重拾多年前未完成的心愿,将家人视为阻拦他成功的伪君子,决心离家开始旅行;哥哥卖掉母亲的手表,跟随父亲开始堕落的生活……“和睦的家庭”分崩离析,人们追随内心最深处的欲望出行,曾经被压抑的不满与苦恼藉此机会通通爆发,恶之花在迷雾中争相开放。
雾中的一切从“我”的视角展开,“我“作为家庭中唯一的“清醒者”,叙说着在雾中我所经历的一切。作者苦心营造着一种变态世界的可感知,第一人称的叙事口吻让叙事接收者不由自主地代入”我“的身份,在作者有意为之的强刺激的感官体验下,读者原本清醒的审视在怪异扭曲的感知下变得模糊,陷入到作者设置的混乱之中,身上仿佛也沾染上一层脱不掉的湿冷。
残雪的小说向来以古怪著称,她喜用一些奇怪的意象,如“淡蓝色的太阳”,“灰老鼠”,“硬邦邦的棉被”,“流汗”,常常让人物躯体的某个部分开始说话,“父亲的脖颈浮在半空中说起话来”,营造出一种惊悚的氛围,她的叙述逻辑也是混乱的,常常出现一种叙事的断裂,复调的强化。她的笔触既有安特莱夫视的阴冷,爱伦·坡式的惊悚,哥特式的阴郁,又有着卡夫卡式的荒诞,余华式的冷静。在不可靠的世界中,人物的真实生存体验往往会呈现得更加清晰,因为当理性的判断无法进行时,人们只能通过某种直接感知去触碰文本。所以,气氛的营造,强有力的感官刺激成了残雪文章最有力的说服武器,恐惧,紧迫,厌恶,仇恨等强烈的情绪发泄在混乱的叙事空间里构成唯一一条主线,人们顺着这条主线走往往能触摸到作者最深的关切。
《雾》中隐藏着一些湿冷的恶之花,这些病态之花,邪恶之花,裹挟着被理智所深深压制着欲望与苦闷,借着不见天日的阴暗空间纷纷生长。在浓雾打造出隐秘而混乱的世界,人与人的亲密关系纷纷崩塌,恶意与怀疑无限喷涌,夫妻之情,父子之情,母子之情,手足之情这些世间上最亲近的感情,在作者的实验下,露出它们的秘密。
“采撷恶之花,是为了在恶中挖掘希望,显示出某种思考和教训来。”
作者用怪异的笔触,在雾中冷漠收割着这些被释放的恶之花,一边剖白,一边战斗,人性的恶被淋漓尽致地挖掘,读者通过冲击感官,直击心灵的感知获得这些痛苦的体验,从而开始深思。《雾》是一场疯狂的战斗,它大胆而横冲直撞的释放罪恶,然后再试图收割罪恶。
“一个灰白的半圆在门边飘荡,探头探脑,那是一团更浓的雾。”浓雾在门口徘徊,更多的恶之花在湿冷中蠢蠢欲动,看来作者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