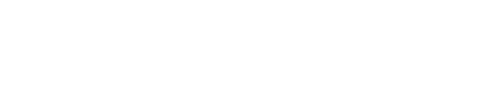那时应是四月,槐树正发花了。
槐花极其素净,一丛丛,一串串,柔软的点点白色挤在一起。它椭圆的叶子,也正是春天的颜色,轻盈欲飞。盛开时,若正逢风起,再加上满枝叶的阳光,那就是一树的流金溢彩,一树的笑靥摇曳。我极爱这花瓣的形状,那大瓣的花舒展着,像是要填满所有,我却总嫌太张扬——这小小的豆科花,只浅浅一笑,便甚得我心意。更何况那甜甜的芬芳呢!还没等走近,便已经香味袭人,沁人心脾了。
我家附近,就有一棵老槐。一日日地日升日落,我一日日地从树下走过,它一日日地吐新,或是凋零。
曾看过《不知有花》:“不为花而目醉神迷,惊愕叹息的,才是花的主人吧。对那山村妇人而言,花是树的一部分,树是山林的一部分,树是山林的一部分,而生活是浑然大化的一部分。她与花就像山与云,相亲相融而不知。”
不如,相忘于天涯。“忘”一字,或许是最好的状态。因为习惯了生命中有你,有时忘了你,也不失为美好。
但离去了,反倒发觉自己不曾真正忘了。
那条小路,槐花飘香,我曾经跳跃着,和你一起笑着跑过夕阳;我曾经在微雨中旋转着伞,看着雨花迸溅;我曾经一个人在暴雨中跑过这条路,泪水和雨水一齐飞洒。
外婆的手艺是极好的,桂花、槐花皆可入糕,入饼。或是做菜时稍稍加一点干花,不仅仅是更香甜了,也让平淡的菜肴增添了一丝花的柔情。
六岁那年,我吃着外婆做的槐花掺着的饼,眼睛里闪烁着星星。
八岁那年,我和发小一起拾起一地的芬芳碎片,再把花儿扬向天空,银铃般的笑声穿过云霄。
九岁那年,我稚嫩的手指抚摸着槐树的粗糙的皮肤,一点一点在心中描绘着光与影的交错。
十四岁那年,我仰头望向槐花,眼里倒映着的却是心心念念的那个男孩的影子。
十五岁那年,我搬家了,临走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望向老槐。
十八岁那年,我看到了这三年没见的老槐,笑着笑着眼中竟有了泪珠。
还是十八岁这年,我即将远行去憧憬远方,并没有丝毫想念这江南的小城。
还是十八岁这年,我默默写下这些文字,单曲循环着:“唱着晨曦,码头陪你看晚霞,我想和你留在我的家,花开花落匆匆了年华。”不知为何竟留下泪来,给高中同桌的对话框中敲下了三个字:“我哭了。”
这里没有槐树啊,不曾看到一束槐花的欢笑啊。
是夜,夜色深沉。
我陷在夜的柔软里。我跌倒在夜的碎片里。我想听你的故事,我想讲讲我的故事——彻夜不眠。忽然好想你,我听着那飘着的歌,泪水就这样流下来。或许荒唐,或许轻狂,可我,
仍在思念着一个人的双眸。
此刻,窗外渐渐响起雨声了。
真有种“窗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,罗衾不耐五更寒”的诗意了。又念起了那首词:“晓来后,一池萍碎,春色三分,二分尘土,一分流水。”当时甚是爱此词,春愁不比秋殇,春愁总归还是明丽的,雨后见到了清清朗朗的阳光时,便得豁然的心境了,却也不免对残花慨叹几句罢了。
雨声又渐歇了,绿色裙子的姑娘也该回屋了。